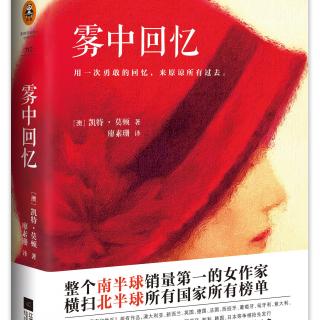
介绍:
去年十一月,我做了一场噩梦。
梦回一九二四年,我重返里弗顿。所有的门大敞,丝质窗帘在夏日和风中掀起微澜。天气温煦,山丘高处的古老枫树下,一支交响乐团悠然演奏,轻快的小提琴声在暖风中飘荡。空气中不时扬起明朗清脆的笑声和水晶相碰的叮当声,天空如此湛蓝,而我们一度以为这一切早已被战争永远地摧毁。一名男仆身着帅气英挺的黑白制服,自细长酒杯垒就的塔顶倾倒香槟,众人拍手叫好,为眼前这份奢华兴奋不已。
就像每个人都曾梦见的一样,我看见自己在宾客中缓慢移动,比现实中的步履更加迟缓,周围的人则化为丝绸和亮片形成的朦胧影像。
我在寻找某个人。
景象一变,我站在避暑别墅附近,不是里弗顿的避暑别墅,不可能是,也不是泰迪 设计的堂皇崭新的建筑,而是一座古老的房舍,常春藤爬满墙壁,在窗户间缠绕盘旋,扼住廊柱,让它们看起来行将窒息。
有人在呼唤我,一个女人。我认得这个声音。呼唤从建筑后方的湖畔传来。我走下山坡,双手掠过高高的芦苇,一个身影蜷伏在堤岸上。
那是汉娜,穿着结婚礼服,泥渍紧紧黏在玫瑰刺绣上,溅满前襟。她抬头望着我,隐没在阴影中的面孔异常苍白。她的声音使我的血液似乎都凝固了。“你来得太迟了,”她指着我的双手,“太迟了。”
我低头看自己的手。一双年轻的手沾满黑色河泥,捧着一条猎狗僵硬冰冷的尸体。
我当然知道为何会做这个噩梦,因为一封来自一位电影导演的信。这些日子,我很少收到信,只有度假的朋友出于责任偶尔寄来的问候明信片、银行循例寄来的敷衍信件,还有小孩洗礼仪式的邀请函,它们令我震惊地发现那些孩子的父母早已不是小孩了。
十一月下旬的一个星期二早上,乌苏拉的信抵达,是西尔维亚来帮我铺床时带来的。她高高扬起修饰得十分浓密粗厚的眉毛,挥舞着信封。
“今天有信,看邮票是从美国寄来的,也许是你孙子?”她的左眉高高挑起,形成一个问号,声音却越来越低,渐成沙哑的低语。“真是太不幸了,那件事 真的,他是那么年轻有为。”
我打断西尔维亚的感叹,说了些谢谢她帮我取信之类的话。我喜欢西尔维亚。她能看到隐藏在我脸上条条皱纹之下那个二十岁的女孩,而这样的人不多。尽管如此,我仍然不想和她谈论马科斯。
我请她拉开窗帘,她紧抿着唇,片刻后转而提起另一个她喜欢的话题 天气,说什么圣诞节可能迎降大雪,这会给罹患关节炎的老人带来不适。我只在必要时答话,心思仍滞留在落于腿面的信封上,吃惊于潦草的笔迹、外国邮票和已变柔软的信封边缘,看来它已经过漫长的旅程。
“要不我念给你听吧,”西尔维亚的语气中充满期待,她最后一次用力拍拍枕头,“好让你的眼睛休息一下。”
“不用了,谢谢你。请将眼镜递给我好吗?”
她承诺打扫完毕就回来帮我穿衣服。她一离开,我立即撕开信封,双手剧烈地颤抖着,想知道他是不是终于决定返回家乡。
写信的不是马科斯,而是一位年轻女性。她正在拍摄一部有关过去的电影,想请我去看看拍摄场景,故地重游,缅怀久远的如烟往事,仿佛那不是我耗尽一生假装遗忘的一切。
我没有理会信中的请求,只是小心翼翼地将它折好,静静夹进一本早就不读的书里,然后长舒了一口气。这不是我第一次因外界原因想起里弗顿的过往,想起罗比 和哈特福德姐妹的暧昧情愫。一次,露丝在看一部有关战争诗人的纪录片,我无意间瞟到了结尾。罗比的脸填满整个屏幕,名字工工整整地印在下方,我的心一阵刺痛。然而什么都没发生。露丝毫无反应,旁白者继续述说,我也不停手地擦抹晚餐的盘子。
还有一次在看报纸时,我的视线被“收视指南”里一个熟悉的名字吸引。那是一档回顾七十年来英国电影历程的节目,我记下了播放时间,心却战栗不已,不知自己是否有勇气收看。结果,节目还未结束我就睡着了。
2节目中提到埃米琳的地方不多,只播放了几张宣传照,但没有一张能展现她真正的美艳;还播放了一段她出演的默片,节选自《维纳斯事件》。片中的她看起来十分古怪:双颊瘦削,肢体僵硬,像个木偶。那些几乎被小题大做的其他电影则丝毫未提。我猜,在这个时代,性放纵和生活糜烂都不值一提。
以前,我也曾被迫唤起这些记忆,但这次不一样。七十多年来,这是第一次,有人将我同这些事件联系起来,有人记得在那个夏天,一个叫格蕾丝?里维斯的年轻女子也在里弗顿。忽然被揪出来,这让我多少有些不安和心虚。
不,我毅然下定决心,不回信。
我的确没回。
但怪异的事情发生了。长期蛰伏在幽暗心灵深处的记忆偷偷从裂罅中潜出,影像被高高掷起,画面完美清晰,仿若昨日。然后,恰如第一滴雨试探落地,旋即大雨如注,洪水汹涌,所有对话争先恐后地涌出,鲜活场景如电影上映般一幕接着一幕。
我令自己吃惊。当飞蛾将我近期的记忆啃噬出缺口,我却发现遥远的过去清晰可见。最近它们常常出现,那些过去的鬼魅,而我惊讶自己已不再介意。用一生逃避的幽魂几乎变成一种安慰,我欢迎并期待它们,就如西尔维亚匆忙完成打扫工作,好来得及坐在大厅里观看她总挂在嘴边的电视剧。我想,我已然遗忘,黑暗中总有明亮的记忆。
第二封信于上星期到达,同样柔软的信纸,同样潦草的笔迹。我知道,这次我会答应,答应去看看那些场景。我感到好奇,我已多年不曾有过这种感受。能让一个九十八岁的老人产生好奇的事并不多,我想见见乌苏拉?莱恩,这个对他们的故事抱持非凡热情的人,我想知道她打算如何让他们复活。
我给她回信,请西尔维亚寄出,然后我们安排会晤时间。
里弗顿的起居室(1)
我的头发以前一直是浅色的,现在则白如丝绵,长而柔软。随着时光流逝,它似乎愈发柔顺。我以头发为傲,上帝知道我没有多少引以为傲的了,或许再也不会有。这头长发已随我多年,从一九八九年直到现在。我的确很幸运,西尔维亚喜欢为我梳发编辫,哦,她的动作那么轻柔,日复一日。这并不属于她的工作范围,对此我非常感激。我一定得记得将这份感激告诉她。
由于太过兴奋,今早我还是错过了机会。西尔维亚拿来果汁时,我根本喝不下。那条整个星期都向我体内灌注精力与能量的神经,一夜之间绕成死结。她帮我穿上崭新的桃色套装,是露丝买给我的圣诞节礼物,又将我脚上的拖鞋换成外出鞋,这双鞋通常待在我的衣柜里等着腐朽。外出鞋的皮革十分坚硬,西尔维亚得用力提拽才能为我套上,但这样穿才算体面。我已经老得适应不了新的礼数,无法像院内比我年轻的同伴那样穿着拖鞋出门。
腮红能为双颊染上一丝生气,但我很小心,不让西尔维亚刷得太多,唯恐自己看起来像个殡葬人偶。事实上,一点儿腮红已很不自然,其余部分的我显得那么苍白,瘦小。
我颇费了一番力气才将黄金坠饰项链挂在脖子上。可以放照片的坠饰散发着十九世纪的优雅风韵,和我身上这套现代实用风格的衣服很不协调。我调整项链时对自己的大胆感到不解,不知露丝看到后会怎么说。
视线下坠,落在化妆台上的小型银制相框上。我的婚礼照片。其实不将它放在那里,我也不会难过,那场婚姻太过久远,而且为时短暂,可怜的约翰。但这是我对露丝的让步。或许,以为我仍为他消瘦会令她开心。
西尔维亚搀扶着我进入起居室 这个字眼儿仍然使我心痛 大家在这里吃早餐,而我在等待露丝,她同意开车载我去谢伯顿制片厂,尽管她说自己不该这么做。让西尔维亚把我安置在角桌旁,再端来一杯果汁后,我开始重读乌苏拉的来信。
八点半,露丝准时到达。也许对这次出门她感到不安,但仍像往常一样准时。我听说,在艰困时期出生的孩子永远无法摆脱灾难的阴霾,露丝便证实了这一点。她出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西尔维亚迥然不同,后者只年轻十五岁,却总是对紧身裙小题大做,笑起来肆无忌惮,每交一个新男友就变换发色。
这个早晨,穿过起居室的露丝衣着讲究,装扮一丝不苟,但比篱笆桩还要僵硬。
“早安,妈妈。”她冰冷的嘴唇划过我的脸颊。“吃完早餐了吗?”她盯着我面前喝了一半的果汁,“希望你多吃点。我们可能会碰到早高峰的交通阻塞,没时间停下来吃东西。”她看看表,“想上厕所吗?”
我摇摇头,纳闷自己何时变成了孩子。
“你戴着父亲的坠饰项链,我好久没看到它了。”她伸手将它摆正,点点头表示赞许,“他的眼光不错,不是吗?”
我表示同意,这是我在她年幼时撒的小谎,而她至今仍然坚信不移令我动容。看着敏感易怒的女儿,我胸中涌起一股怜爱,但它很快被年迈父母力不从心的负疚感压倒。每每面对她忧虑的脸庞,这种感觉就不由得升起。
她扶着我的手臂,把拐杖放进我另一只手中。许多人偏爱助行器或电动轮椅,但我用拐杖就很好,我已经习惯了,不想为任何理由改变。
我的露丝是个好女孩,稳重可靠。她今天的着装很正式,像是要去拜访律师或医生。我知道她一定会精心打扮。她想给人留下好印象,想让这位电影导演知道,不管母亲过去从事什么职业,露丝?布拉德利?麦考特都是个受人尊敬的中产阶级,这一点不容置疑。
我们沉默地坐在车上,没过多久,露丝开始调收音机。她的手指已显老态,早上强迫自己套上的戒指使得指关节略显浮肿。看见自己的女儿渐趋老迈,令人震惊。我不由得瞥了一眼放在自己腿上的双手。那双过去异常忙碌、娴熟履行仆人繁复工作的手,如今灰暗无力,迟钝不堪。露丝最终决定收听古典音乐。电台主持人愚蠢空洞地说完他的星期日时光,开始播放肖邦的乐曲。这真是个巧合,我今天确实该听《升C小调圆舞曲》。
. . . . . .
大家还在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