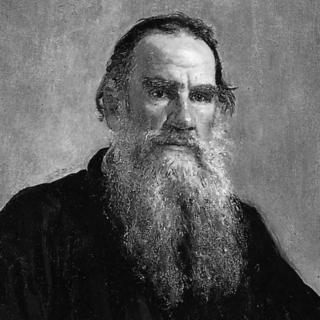
介绍:
“你们说,一个人本身不可能了解什么是好,什么是坏,问题全在环境,是环境坑害人。我却认为问题全在偶然事件。拿我自己来说吧……”
我们谈到,为了使个人变得完善,首先必须改变人们的生活条件,接着,人人尊敬的伊凡·瓦西里耶维奇就这样说起来了。其实,谁也没有说过自身不可能了解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只是伊凡·瓦西里维奇有个习惯,总爱解释他自己在谈话中产生的想法,然后为了证实这些想法,讲起他生活里的插曲来。他时常把促使他讲述的原因忘得一干二净,只管全神贯注地讲下去,而且讲得很诚恳、很真实。
现在他也是这样做的。
“拿我自己来说吧。我的整个生活成为这样而不是那样,并不是由于环境,完全是由于别的原因。”
“到底由于什么呢?”我们问道。
“这可说来话长了。要讲老半天,你们才会明白。”
“您就讲一讲吧。”
伊凡·瓦西里耶维奇沉思了一下,又摇摇头。
“是啊,”他说,“我的整个生活在一个夜晚,或者不如说,在一个早晨,就起了变化。”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是这么回事:当时我正在热烈地恋爱。我恋爱过多次,可是这一次我爱得最热烈。事情早过去了;她的女儿们都已经出嫁了。她叫B——,是的,瓦莲卡·B——” 伊凡·瓦西里耶维奇说出她的姓氏,“她到了50岁还是一位出色的美人。在年轻的时候,18岁的时候,她简直能叫人入迷;修长、苗条、优雅、庄严——正是庄严。她总是把身子挺得笔直,仿佛她非这样不可似的,同时又微微仰起她的头,这配上她的美丽的容貌和修长的身材——虽然她并不丰满,甚至可以说是清瘦,就使她显出一种威仪万千的气概,要不是她的嘴边、她的迷人的明亮的眼睛里,以及她那可爱的年轻的全身有那么一抹亲切的、永远愉快的微笑,人家便不敢接近她了。”
“伊凡·瓦西里耶维奇多么会渲染!”
“但是无论怎么渲染,也没法渲染得使你们能够明白她是怎样一个女人。不过问题不在这里。我要讲的事情出在40年代。那时候我是一所外省大学的学生。我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那时我们大学里没有任何小组,也不谈任何理论,我们只是年轻,照青年时代特有的方式过生活,除了学习,就是玩乐。我是一个很愉快活泼的小伙子,而且家境又富裕。我有一匹剽悍的溜蹄马,我常常陪小姐们上山去滑雪(溜冰还没有流行),跟同学们饮酒作乐(当时我们只喝香槟,没有钱就什么也不喝,可不像现在这样改喝伏特卡)。但是我的主要乐趣在参加晚会和舞会。我跳舞跳得很好,人也不算丑陋。”
“得啦,不必太谦虚。”一位交谈的女伴插嘴道,“我们不是见过您一张旧式的银板照片吗?您不但不算丑陋,还是一个美男子哩。”
“美男子就美男子吧,反正问题不在这里。问题是,正当我狂热地恋爱她的期间,我在谢肉节的最后一天参加了本省贵族长家的舞会,他是一位忠厚长者,豪富好客的侍从官。他的太太接待了我,她也像他一样忠厚,穿一件深咖啡色的丝绒长衫,戴一条钻石头饰,她袒露着衰老可是丰腴白皙的肩膀和胸脯,好像伊丽莎白·彼得罗夫娜的画像上画的那样。这次舞会好极了:设有乐队楼厢的富丽的舞厅,属于爱好音乐的地主之家的、当时有名的农奴乐师,丰美菜肴,喝不尽的香槟。我虽然也喜欢香槟,但是并没有喝,因为不用渴酒我就醉,陶醉在爱情中了。不过我跳舞却跳得精疲力竭——又跳卡德里尔舞,又跳华尔兹舞,又跳波尔卡舞,自然是尽可能跟瓦莲卡跳。她身穿白衣,束着粉红腰带,一双白羊皮手套差点齐到她的纤瘦的、尖尖的肘部,脚上是白净的缎鞋。玛祖卡舞开始的时候,有人抢掉了我的机会:她刚一进门,讨厌透顶的工程师阿尼西莫夫——我直到现在还不能原谅他——就邀请了她,我因为上理发店去买手套,来晚了一步。所以我跳玛祖卡舞的女伴不是瓦莲卡,而是一位德国小姐,从前我也曾稍稍向她献过殷勤。可是这天晚上我对她恐怕很不礼貌,既没有跟她说话,也没有望她一眼,我只看见那个穿白衣服、束粉红腰带的修长苗条的身影,只看见她的晖朗、红润、有酒窝的面孔和亲切可爱的眼睛。不光是我,大家都望着她,欣赏她,男人欣赏她,女人也欣赏她,虽然她盖过了她们所有的人。不能不欣赏她啊。”
“照规矩可以说,我并不是她跳玛祖卡舞的舞伴,而实际上,我几乎一直都在跟她跳。她大大方方地穿过整个舞厅,径直向我走来,我不待邀请,就连忙站了起来,她微微一笑,酬答我的机灵。当我们被领到她的跟前而她没有猜出我的代号时,她只好把手伸给别人,耸耸她的纤瘦的肩膀,向我微笑,表示惋惜和安慰。当大家在玛祖卡舞中变出花样,插进华尔兹的时候,我跟她跳了很久的华尔兹,她尽管不断地喘息,还是微笑着对我说:‘再来一次’。于是我再一次又一次地跳着华尔兹,甚至感觉不到自己还有一个重甸甸的肉体。”
“咦,怎么会感觉不到呢?我想,您搂着她的腰部的时候,不但能够清楚地感觉到自己的肉体,还能感觉到她的哩。”一个男客人说。
伊凡·瓦西里耶维奇突然涨红了脸,几乎是气冲冲地叫喊道:“是的,你们现代的青年就是这样。你们眼里只有肉体。在我们那个时候可不同。我爱得强烈,就越是不注意她的肉体。你们现在只看到腿子、脚踝和别的什么,你们恨不得把所爱的女人脱个精光;而在我看来,正像阿尔封斯·卡尔——他是一位好作家——说的:我的恋爱对象永远穿着一身铜打的衣服。我们不是把人脱个精光,而是要设法遮盖他的赤裸的身体,像挪亚的好儿子一样。得了吧,反正你们不会了解……”
“不要听他的。后来呢?”我们中间的一个问道。
“好吧。我就这样跟她跳,简直没有注意时光是怎么过去的。乐师们早已累得要命——你们知道,舞会快结束时总是这样——翻来覆去演奏冯祖卡舞曲,老先生和老太太们已经从客厅里的牌桌旁边站起来,等待吃晚饭,仆人拿着东西,更频繁地来回奔走着。这时是两点多钟。必须利用最后几分钟。我再次选定了她,我们已经沿着舞厅跳到一百次了。”
“‘晚饭以后还跟我跳卡德里尔舞吗?’我领着她入席的时候问她。”
“‘当然,只要家里人不把我带走。’她微笑着说。
“‘我不让带走。’我说。
“‘扇子可要还给我。’她说。
“‘舍不得还。’我说,同时递给她那不大值钱的白扇子。
“‘那就送您这个吧,您不必舍不得了。’说着,她从扇子上撕下一小片羽毛给我。
“我接过羽毛,只能用眼光表示我的全部喜悦和感激。我不但愉快和满意,甚至感到幸福、陶然,我善良,我不是原来的我,而是一个不知有恶、只能行善的超凡脱俗的人了。我把那片羽毛藏进手套中,呆呆地站在那里,再也离不开她。
“‘您看,他们在请爸爸跳舞。’她对我说道,一面指着她的身材魁梧端正、戴着银色肩章的上校父亲,他正跟女主人和其他的太太们站在门口。
“‘瓦莲卡,过来。’我们听见戴钻石头饰、生有伊丽莎白式肩膀的女主人的响亮的声音。
“瓦莲卡往门口走去,我跟在她后边。”
“‘我亲爱的,劝您父亲跟您跳一跳吧。喂,彼得·符拉季斯拉维奇,请。’女主人转向上校说。
“瓦莲卡的父亲是一个很漂亮的老人,长得端正、魁梧,神采奕奕。他的脸色红润,留着两撇雪白的尼古拉一世式的卷曲唇髭和同样雪白的、跟唇髭连成一片的络腮胡子,两鬓的头发向前梳着,他那明亮的眼睛里和嘴唇上,也像她女儿一样,露出亲切快乐的微笑。他生成一副堂堂的仪表,宽阔的胸脯照军人的派头高挺着,胸前挂了几枚勋章,此外他还有一副健壮的肩膀和两条匀称的长腿。他是一位具有尼古拉一世风采的宿将型的军事长官。
“我们走这门口的时候,上校推辞说,他对于跳舞早已荒疏,不过他还是笑眯眯地把手伸到左边,从刀剑带上取下佩剑,交给一个殷勤的青年,右手戴上麂皮手套,‘一切都要合乎规矩。’他含笑说,然后抓住女儿的一只手,微微转过身来,等待着拍子。
“等到玛祖卡舞曲开始的时候,他灵敏地踏着一只脚,伸出另一只脚,于是他的魁梧肥硕的身体就一会儿文静从容地,一会儿带着靴底踏地声和两脚相碰声,啪哒啪哒地、猛烈地沿着舞厅转动起来了。瓦莲卡的优美的身子在他的左右翩然飘舞,她及时地缩短或者放长她那穿白缎鞋的小脚的步子,灵巧得叫人难以察觉。全厅都在注视这对舞伴的每个动作。我却不仅欣赏他们,而且受了深深的感动。格外使我感动的是他那被裤脚带箍得紧紧的靴子,那是一双上好的小牛皮靴,但不是时兴的尖头靴,而是老式的、没有后跟的方头靴。这双靴子分明是部队里的靴匠做的。‘为了把他的爱女带进社交界和给她给穿戴打扮,他不买时兴靴子,只穿自制靴子,’我想。所以这双方头靴格外使我感动。显然有过舞艺精湛的时候,可是现在发胖了,要跳出他竭力想跳的那一切优美快速的步法,腿部的弹力已经不够。不过他仍然巧妙地跳了两圈。他迅速地叉开两腿,重又合拢来,虽说不太灵活,他还能跪下一条腿,她微笑着理了理被他挂住的裙子,从容地绕着他跳了一遍,这时候,所有的人都热烈鼓掌了。他有点吃力地站立起来,温柔、亲热地抱住女儿的后脑,吻吻她的额头,随后把她领到我的身边,他以为我要跟她跳舞。我说,我不是她的舞伴。
“‘呃,反正一样,您现在跟她跳吧。’他说,一面亲切地微笑着,把佩剑插进刀剑带里。
“瓶子里的水只要倒出一滴,其余的便常常会大股大股地跟着倾泻出来,同样,我心中对瓦莲卡的爱,也放发了蕴藏在我内心的全部爱的力量。那时我真是用我的爱拥抱了世界。我爱那戴着头饰、生有伊丽莎白式的胸部的女主人,也爱她的丈夫、她的客人、她的仆役,甚至也爱那个对我板着脸的工程师阿尼西莫夫。至于对她的父亲,连同他的自制皮靴和像她一样的亲切的微笑,当时我更是体验到一种深厚的温柔的感情。
“玛祖卡舞结束之后,主人夫妇请客人去用晚饭,但是B上校谢绝了邀请,他说他明天必须早起,就向主人告辞了。我惟恐连她也给带走,幸好她跟母亲留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