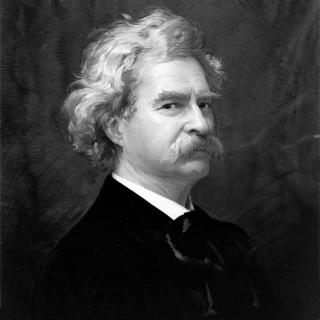
介绍:
去年春天我去芝加哥看博览会,虽然结果没看成功,但是我在那次旅程中却不是毫无收获——可以说,它给了我一些补偿。在纽约,我经过介绍认识了一位正规军队中的少校,他说要去看博览会,于是我们约好一同上路。我必须先去波士顿,但这并不碍事,他说愿意一道去,不妨多花上一些时间。他这人仪表漂亮,体格魁梧得像一位斗士,但举止温和,谈话娓娓动听。他为人十分可亲,但又显得很沉着。可不是,他是完全缺乏幽默感的。他对四周的事都深感兴趣,然而他那宁静的神态却始终不受外界的影响;任何事物都不能干扰他,任何事物都不能激动他。
但是,过了还不到一天,我已经发现,尽管他外表是那么冷静,但在他内心深处什么地方却蕴藏着一股热情——热衷于破除那些在琐细行为中表现出的种种陋习。他要维护公民的权利——这是他的好癖。他的想法是:共和国的每个公民都必须把自己看作是一个非官方的警察,不受任何报偿,经常监视维护着守法与执法情况。他认为,要维护和保障公众的权利,惟一有效的方法就是要求每个公民都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去防止或惩罚他本人看到的那些违法乱纪行为。
这可是一个很好的设想,但是我认为一个人这样做会经常卷入麻烦;我觉得,一个人这样做,无异于试图开除一个犯了过失的小公务员,而结果他也许会招来人家嘲笑。如是他说事实并非如此,说我的想法是错误的;说那样做从来也不会使任何人被开除;而且,实际上你绝不可以让任何人被开除了;因为你那样做本身就是一次失败;不,我们必须改造那个人——要把他改造过来,要使他成为一个称职有用的人。
“是不是我们必须先去告发那犯了过失的人,再请他的上级不要开除他,只要训斥他一顿,然后仍旧留用他吗?”
“不,我不是那意思;你根本就不要去告发他,因为,如果那样做,他就会有打碎饭碗的危险。你可以做得像是要去告发他——那也只是到了任何其他方法都不起作用的时候。那是极端的例子。那样就是使用威力,而威力是有害的。有效的方法是运用权术,喏,如果一个人富有机智——如果一个人肯运用权术——”
我们在电报局的一个窗口足足站了两分钟,少校一直设法引起一个年轻报务员的注意,几个报务员都只顾逗乐取笑。这时候少校发话了,他唤其中一个报务员接收他的电报。可是他得到的答复是:
“我想您可以等待一会儿,行吗?”这句答话一说完,他们又把玩笑话说开了。
少校说他可以等待,并不赶急。接着,他又拟了一份电报:
西联电报公司经理:
今晚请过来和我共餐。我可以把你某分局如何经营业务的情况说给你听。
稍停,那个不久前说话那么傲慢无礼的年轻人伸出手来接过了电报稿,他刚读完电文,脸色就变了,他开始又是道歉又是解释。他说,如果这份害人的电报发了出去,他就要被辞退,也许永远找不到另一个这样的职位。如果能饶恕他这一次,他以后就再也不做人家会提意见的事情了。少校接受了这一表示让步的请求。
我们走开后,少校说:
“喏,您明白了吗,那就是我运用权术——而且,您明白那是怎样发挥作用的了。一般人总是爱进行恫吓,那种做法没好处——因为那小伙子总是会舌剑唇枪,跟你针锋相对地来上一套,结果你几乎总是会输给他,让自己出丑的。可是,您瞧,权术这玩意儿他是对付不了的。温和的语言加上权术——这就是我们应当使用的工具。”
“是了,我明白了,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您那样的机会呀。并不是每个人都和西联电报公司经理那样有交情呀。”
“哦,您误解了我的意思。我并不认识那位经理——我只是为了要运用权术而利用了他一下。这是为了他的好处,也是为了公众的好处。这样做是没害处的。”
我不肯随声附和,只吞吐其词地说:
“可是,说谎也会是正当的,或者高贵的吗?”
他并不注意这句问话中那种委婉含蓄的、自以为是的意味,他只是不动声色、稳重而简单地回答说:
“是呀,有时候是的。为损人而说谎,为利己而说谎,这是不正当的,然而,为了有助于别人而说谎,为了有利于公众而说谎——瞧,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这是一条谁都知道的道理。不必计较所采用的手段怎样:你只要看收到的效果如何。刚才那样一来,那小伙子就会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就会变得循规蹈矩。他是一个要面子的人。像他那样的人是值得挽救的。可不是,即使不是为了他本人,单是为了他母亲,也是值得挽救他的。他肯定有母亲在——还有姊妹们。该死,那些人老是忘了这一点!您可知道,我这辈子从来没参加过决斗——一次也没参加过——虽然像其他人一样,我也曾遇到过挑衅。我每一次都能看到那个人的无辜的老婆和小孩站在他和我之间。他们并没有招谁惹谁——你瞧,我可不能伤了他们的心。”
就是那一天内,他纠正了许多人们的小动作中所表现的陋习,但始终没引起摩擦——总是运用巧妙而漂亮的“权术”,事后别人并没感到难堪,而他本人却从那些行动中得到了很大的快乐与满足,最后我不禁羡慕他所干的这一行——心想:如果需要时我也能够很有把握地在言语上偏离开事实,就像我自信经过一些练习后能够在印刷品的掩护下用笔墨所做到的那样,或许我也要采用这种办法哩。
那天夜晚,很迟的时候我们才离开当地,乘铁路马车去市区,三个喧闹粗暴的家伙登上了车,开始在一群胆小怕事的乘客中(他们有的是妇女和儿童)左顾右盼,任意地嘲笑,说的都是些污秽轻薄的语言。没一个人敢反抗或者劝阻他们,列车员试图好言以理相喻,但是那些恶棍只顾辱骂和嘲笑他。我很快就看出,少校已经意识到这是属于他所管的事情;显然,他是在盘点自己脑子里储存的权术,正在进行准备。我想,在这个场合,只要是一句玩弄权术的话说出了口,他就会招来劈头盖脸一大堆嘲笑,也许还会导致比这更加难堪的后果;然而,为时已经过晚,我还没来得及悄声劝阻他,他已经开口了。他用平缓而冷静的口气说:
“列车员,您必须把这些猪赶下去。让我来帮助您。”
这可是我没料到的。一眨眼工夫,三个恶棍已经向他扑过来。但是他们一个也没能接近他。他挥出了三拳,你真想不到会在拳击场以外看到那样猛烈的打击,只打得那三个人一个也没力气再从倒下的地方站起来。少校拖开了他们,把他们赶下了车,我们的车又继续前进。
我感到惊奇,惊奇的是看到一个温驯得像头羔羊的人竟然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惊奇的是他显示出那样强大的力量,取得了那样全面的、彻底的胜利;惊奇的是他把整个这件事情做得利落而又有条不紊。由于想到整天里都听到这个“打桩机”侈谈应当怎样进行委婉的劝导和运用温和的权术,我就觉得现在的情形具有它幽默的一面,于是我想促使他注意到这一点,并且就此说上几句嘲笑的话;然而,我再向他一打量,就知道那样做将是徒劳的——因为他那副怡然自得的神情并不含有丝毫幽默感;他是不会理解我的话的。我们下车后,我说:
“那可是一套精彩的权术呀——实际上是三套精彩的权术。”
“那个吗?那不是什么权术。您根本没弄懂。权术完全是另一码事。对那种人你不能运用权术;他们对权术不会理解。不,那不是权术,那是威力。”
“瞧您提到了它,我……可不是,我想您这话大概说对了。”
“说对了?我当然说对了。那就是威力。”
“我也认为,从外表上看来它是威力。您常常需要用那种方式改造人吗?”
“绝对不是。那种情形极少发生。半年里不会多过一次。”
“那几个人受了伤会复原吗?”
“会复原?这还用说,他们肯定会复原的。他们绝对不会有危险。我知道应该怎样揍,应该揍在哪儿。您注意到,我并没揍他们颚骨底下。那样会要他们命的。”
我相信这话是实。我说(我认为自己说得挺俏皮),他整天里一直像只羊羔,可是这会儿突然变成一头公羊——一头撞角的公羊;但是他却显得那么恳挚可爱,一本正经地说我讲得不对,说什么撞角羊完全是另一样东西,现在人们已经不再使用它。他这话叫人听了生气,我差点儿脱口而出,说他像个傻子,一点儿也不会欣赏俏皮话儿——说真的,这句话已经迸到舌尖,但是我没说出口,因为知道现在不必急,还是等以后什么时候在电话里说吧。
第二天下午,我们出发去波士顿。特等客车吸烟室里已经客满,于是我们走到普通吸烟室里。过道那边顺座上坐着一个态度温和、样子像农民的老人,他面色苍白,正用一只脚钩住那扇开着的门,想要透点儿新鲜空气。过了不一会儿,一个身材高大的制动手闯进车厢,走到门前停下,恶狠狠地瞪了农民一眼,然后猛地把门一拉,差点儿把老人的皮靴都给带走。接着他又匆匆地赶着张罗他的事情去了。有几个乘客笑起来,老先生露出了一副又羞又恼的可怜神气。
停了不多一会儿,列车员走过,少校拦住他,用习惯的客气态度提出这个问题:
“列车员,如果制动手的举动有不对的地方,乘客该去哪报告?是向您报告吗?”
“如果要告他,您可以到了纽黑文站去告。他做错什么事了?”
少校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列车员好像乐了。他温和的口气中微含讥嘲地说:
“您的意思好像是说,那个制动手并没说什么。”
“是的,他没说什么。”
“可是您说,他恶狠狠地瞪了一眼。”
“是的。”
“后来就粗鲁地拉开了那扇门。”
“是的。”
“全部经过就是这些,对吗?”
“对,那就是全部经过。”
列车员乐呵呵地笑了,他说:
“好吧,如果您要去告他,那是可以的,可是我不大明白,这究竟算得了什么呢。您会说——我这是根据您说的话猜想的——那个制动手侮辱了这位老先生。那么,他们就会问您,他说了一些什么。您说,他根本什么也没说。那么,我估计他们就会说,既然您自己承认他一句话也没说,那您又怎么能断定那是一次侮辱呢?”
列车员这一席无懈可击的说理,引起了漠漠一片赞许之声,这使他感到很高兴——这你可以从他脸上看出来。但是少校并不介意。他说:
“瞧,现在您正好接触到提意见的制度中存在的一个明显的缺点。铁路公司的职员们——不但公众有这种想法,而且看来您也有这种想法——都没注意到;除了口头的侮辱以外,还有其他类型的侮辱。所以,也就没人到总办事处去申诉他受到人家在态度上表示的侮辱,包括手势、表情等方式进行的侮辱;然而,这样的侮辱有时候会比任何口
大家还在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