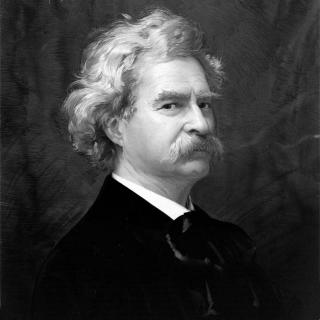
介绍:
怪梦——兼寓规训之意
前天夜里,我做了一个不寻常的梦。仿佛我坐在门口台阶上(也许,那是在某一个城市里),坠入沉思,那时好像是夜间大约十二点或者一点钟光景。天气很美,暗香浓郁悦人。空中悄无人语,连脚步声都听不见。我更觉得四处死一般沉寂,因为,除了偶尔远远传来一条狗的空洞的吠声,以及从更远地方飘来另一条狗更微弱的回应外,没有其他任何声响。稍停,我又听见从街那头回荡过来一阵骨头敲出的呱哒呱哒响声,猜想那大概是一个唱小夜曲的人在敲响板[1]吧。一分多钟过去,一个高大的骷髅,头上罩着一顶兜头帽,身上半遮着一件破碎霉烂的寿衣,衣服的碎布巾儿在一条条的肋骨的骨架两旁拍打着,威风凛凛地踏着阔步在我身边大摇大摆走过去,然后消失在星光闪烁的朦胧灰暗里。他肩上扛着一口破烂的、虫蛀坏了的棺材,手里提着一捆什么东西。我这才知道那是什么在呱哒呱哒响,原来那是这个家伙的骨头节儿碰在一起,他一走路,胳膊就撞着两边的肋骨。不瞒你说,我当时吃了一惊。还没来得及竭力镇定,开始考虑这幽灵预兆的是何吉凶,我只听见又一个走了过来——因为我辨出了他那呱哒呱哒响声。他肩上扛着三分之二的棺材,腋下夹着棺材头尾两块板。我很想向他帽兜底下张一眼,跟他搭讪几句,但是,等到他一走过我身边,回过了头,把深陷的眼眶和暴出的牙齿冲着我笑时,我想还是不留下他为妙。他刚走开,我又听见呱哒呱哒响声,又一个从半明半暗的阴影中显露出来。这一个弯着腰,驮着一块沉甸甸的墓碑,还用绳拖着一口怪寒碜的棺材。他走近我跟前,向我直勾勾地盯了一会儿,然后转过身,把背对着我说:
“可以把这个给我松下来吗?”
我把墓碑往下松,最后把它安放在地上;我这样做时,注意到了碑上刻的姓名是“约翰·巴克斯特·科普曼赫斯特”,死亡的日期是“一八三九年五月”。死者一副疲劳的神情在我身边坐下了,用他的上颌骨擦了擦他的前额骨——我认为这主要是由于他生前的习惯,因为我看不出他拭去了什么汗水。
“真糟糕,真糟糕。”他说,一面把寿衣上残余的破布巾儿向身上拢一拢好,心事重重地用手支着下颏。接着,他就把左脚跷到膝上,开始心不在焉地用一截从棺材里掏出来的霉烂指甲搔他的踝子骨。
“什么事情真糟糕,朋友?”
“咳,所有的一切,所有的一切。我真希望当初要是能够不死就好了。”
“您的话使我感到惊奇。您为什么要说这种话呢?出了什么毛病吗?是怎么一回事?”
“怎么一回事!瞧瞧我这件送终的衣服——这一身破烂货。瞧瞧这块墓碑,它已经被碰得七损八伤。瞧瞧那口羞人的旧棺材。一个人眼看着他的全部家产都要完蛋,您还问他出了什么毛病。他妈的天火烧的!”
“您冷静点儿呀,您冷静点儿呀,”我说,“这情况确实是非常糟——这情况肯定是非常糟,可是,看您已处于目前的状态下,我没想到您还会对这些事十分介意。”
“哼,我的好先生,我对这些事可介意啦。瞧它们损伤了我的自尊心,影响了……也可以说是破坏了我的舒适。如果您允许的话,就让我谈一谈我目前的处境吧——让我原原本本叙述,您听了就会明白。”可怜的骷髅一边说一边把他寿衣上的兜头帽向后推了推,仿佛是准备采取什么行动,但这样一来就不知不觉流露出一副兴致勃勃的神情,那神情非但跟他目前生活(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境况的严重性很不相称,而且跟他愁苦的情绪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您谈下去吧。”我说。
“我就住在这条街上,离开您这儿一两个街区的那片羞人的旧坟地里——哎呀!您瞧,我刚在担心那根软骨会脱下来!——就是从下向上倒数第三根软骨,朋友,请用根细绳儿把它的一头扣在我脊梁骨上吧,如果您手边有这玩意儿的话;不过!要是有一根银丝,那就更加好,而且更耐用,更合适,如果能经常把它摩擦光溜了——一个人,让自己的骨头被这样扯断,被这样拉折压碎,真是不堪设想,何况受这种罪只是由于他的子孙对他漠不关心,根本不去管他啊!”——说到这里,可怜的鬼魂咬牙切齿,我看了那样儿感到一阵心疼,不觉打了一个寒噤——而且由于缺少了那些遮掩的肌肉和表皮,那样儿更大大地加强了恐怖的效果。“我住在那片旧坟地里,到现在已经有三十个年头;可是,告诉您,打我初来的时候起到现在,情况完全改变了:记得我第一次把这副疲劳的老骨头放平在那儿,翻了一个身,再把身子挺直,准备长眠,那时候心里觉得十分舒畅,因为想到此后再没有烦恼、没有悲伤、没有焦急、没有疑惑、没有恐惧,永远没有这一切了,于是我就感到很舒服,感到更满意,听着那教堂里的勤杂工在干活,他光是把第一铲泥土抛在我棺材上,发出吓人的噼啪声,到后来那响声逐渐低沉,变成微弱的轻轻拍打声,那是在给我铺好新居的屋顶呀——多么美呀!啊呀!我真希望您今儿夜里能在那里面试一试!”这时我正在出神,死者就用一只仅剩下骨头的手叭地给了我一巴掌,我被惊醒过来。
“可不是吗?先生,三十年前,我在那儿安息了,日子过得很幸福。因为,当时那地方远远位于乡下——空旷中清风习习,百花盛开,多年的林木一片蓊郁,懒洋洋的微风跟树叶儿窃窃私语,松鼠在我们上空和四周蹿来跳去,那些爬虫都来访问我们,鸟儿奏出的音乐在宁静中四下回荡。啊,当时一个人哪怕少活它十年早死了也是值得的啊!一切都是那么愉快啊。我的邻居们也好,因为所有住在附近的死者都是出自市内的名门望族。看来我们的后代也都关心我们的另一个世界,他们把我们的坟维修得好极了;总是把围栏修得上面没一点儿损坏,经常在棺材的前挡板上涂漆或者粉刷,一发现它们生锈或者烂朽了,就给换上新的;纪念碑总是竖得笔挺的,栏杆从来没人去碰一下,永远灿灿闪亮,玫瑰花和灌木丛都经过了修剪整枝,没一个地方是可以批评的,走道上铺着碎石子,又洁净又平坦。可是,那种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我们的后人已经忘了我们。现在我的孙子住的是一幢用我这双老手挣来的钱建造的很有气派的大厦,可是我却躺在一座没人去过问的坟里,那儿扰人的虫豸咬碎了我的寿衣,然后用碎布去筑它们的虫窝!是我和那些跟我躺在一起的朋友建立了这座美丽的城市,并且使它日趋繁荣,可是结果呢,那些我们抚育出来的、现在变得傲然不可一世的毛头小伙子,却把我们丢在一片被邻居们诅咒,被异乡人揶揄的荒废的公墓里,让我们在那儿腐烂下去。瞧当年和如今有着多么大的差别啊——比如说:现在我们的坟都成了一个个坑;我们棺材的前挡板已经朽烂塌陷;我们的栏杆都东倒西歪,那样儿就像是一个人轻佻无礼地把一只脚跷到了半空中;我们的纪念碑都有气无力地斜靠着,我们的墓碑都无精打采地低垂了头;再没有什么装饰点缀品了——没有玫瑰花,没有灌木丛,没有铺着碎石子的人行道,没有任何看上去可以使你感到舒适的东西;就连那油漆剥落了的旧板条围墙,一度表示不让我们和野兽为伍,不让我们被漫不经心的人践踏的,也逐渐摇摇晃晃,终于倒塌在路旁,只会引人注意到我们落到这样凄凉的归宿地里,招来更多的嘲笑。再说,现在我们再也不能把自己的寒酸情景和破烂衣着隐藏在那片亲切可爱的树林里了,因为城市已经远远伸出它那肃杀的双臂,把我们一股脑儿都圈了进去,于是我们的老家里再没有欢乐的气氛,单剩下那一簇愁人的林木,它们已经对城市生活感到厌倦,就那样竦立在那儿,把脚伸进了我们的棺材,一面眺望那迷蒙的远景,希望自己也能生长在那里。对您说了吧,这情况真羞死人啦!
“现在您开始理解了吧——您总开始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了吧。我们的子孙,就在这城里我们的附近,花我们的钱,过豪华的生活,可我们却不得不苦苦地挣扎,才能把脑袋和骨头保持在一块儿。我的天哪,我们的公墓里没一座坟不是漏水的——没一座坟哪。每一次夜里下雨,我们就得爬出来,歇在树上——有时候我们突然惊醒,因为冰冷的水滴在我们后颈窝里了。告诉您吧,那时候一些多年的旧坟会向上掀起,墓碑被纷纷踢翻,瞧那些老骷髅向树林里那一阵乱奔呀!老天保佑,如果您曾经在这样一个夜晚,十二点以后,走过那个地方,您也许会看到过我们:人数可以多达十五个,都是一只脚站着,骨头节怪可怕地呱哒呱哒响着,风吱喽喽地在我们肋巴骨空隙当中吹过去!有好多次,我们在那些树上怪沉闷地歇了三四个小时,然后爬下来,浑身冻僵,瞌睡朦胧,彼此借用脑壳去舀干净我们墓穴里的水——如果我现在把头向后仰起,您从下面向我嘴里看上一眼,您就可以看到我脑瓜子里一半都成了已经干了的陈旧沉淀——瞧这些东西有时候害得我头昏脑涨、思路迟钝不灵!可不是,先生,您如果是刚巧在破晓前来到这儿,那您就会不止一次地看到我们正在舀墓穴里的水,把我们的寿衣晾在篱笆上。啊,想起来了,我从前有一件很考究的寿衣,一天早晨在那里被偷走了——我猜想那是一个叫史密斯的家伙偷的,他就住在那边的一片乱坟地里——我之所以这样猜想,是因为我第一次看见他的时候,他身上只穿着一件格子布衬衫,可是上一次在新公墓的交谊会上看见他的时候,他竟然成了所有尸体中打扮得最漂亮的一个——再有一件事很能说明问题,他一见我就溜了;没过一会儿工夫,这儿的一个老太婆就遗失了她的棺材——平时她无论上哪儿,总是把它随身带着,因为,如果多受了夜里的寒气,她就会着凉,就会发痉挛性风湿痛,当初她就是害这病送了命。她叫霍奇基斯——安娜·玛蒂尔妲·霍奇基斯——也许您认识她吧?她上边剩下了两颗门牙,个子挺高,可是最爱那样哈着腰,身体左边缺了一根肋骨,脑袋左边搭拉着一绺褪了色的头发,就在右耳朵上边,稍许前面一点儿,翘起着一小撮鬓毛,下巴颏的一边已经松泛,用一根银丝扣着,左边前臂的小骨头丢了——那是在一次打架的时候丢的——她走起路来有着那么一副趾高气扬的神态,一种‘英姿飒爽’的劲头,两臂叉腰,鼻子眼儿仰对着上空——她一向行动自由自在,可是浑身已经七损八伤,到后来她那样儿简直像是一个破烂的陶器篓子——也许,您见过她吧?”
“别倒我的霉啦!”我不由得迸出了这么一句,因为,不知怎地,我当时没料到他会有这么一问,问得有点儿出乎我的意料。但是,我赶紧纠正了我的粗暴的口气,
大家还在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