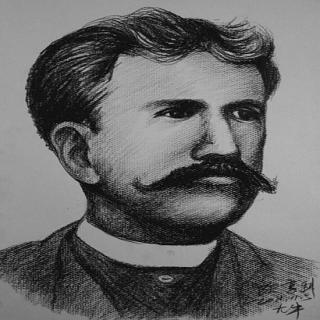
介绍:
读一读一个四条腿的动物所做的文章,我想不会使你们这些作为万物主宰的人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发生动摇。作家吉卜林先生和其他许多人都证实,动物能用英语进行自我表达并由此给人带来稿酬。除了几种旧式月刊仍在刊登布赖和培和培雷火山大爆发的照片外,如今没有哪份杂志不发表动物的故事。
不过诸位别指望我这篇东西里也会讲出一个形象生动,反响非常的故事来,就像丛林系列书刊里所讲的宝宝熊、美美蛇、乖乖虎之类的故事一样。我是一条黄狗,大半辈子都生活在纽约一套廉价的公寓里,睡在墙角一件旧缎纹布衬裙(她参加朗硕曼夫人的宴会时用葡萄酒把这件衬裙污染了)上。诸位不必期望我的狗话能讲究什么艺术手法。
我一生下来就是条小黄狗;出生日期,出生地,家世及初生体重等我一概不知。我最早记得的一件事是一个老太婆用篮子提着我,在百老汇和二十三号街交叉口跟一个胖女人讨价还价,想把我卖掉。哈巴德老婆子一下子把我捧上了天,说我是纯正的波美拉尼亚-汉布东尼安-红爱尔兰-交趾***-斯托克-鲍吉斯猎狐狗。胖女人把手伸进购物袋,在厚斜纹法兰绒布样中间翻找了半天,最后抓出一张五元钞交给对方,算是把我买下了。打这儿以后,我成了一个宠儿——成了一个婆娘的醉心可意、爱不释手的心肝宝贝。唉,尊敬的读者,一个重二百磅的女人,满嘴法国卡门贝软干酪和西班牙脆皮的味儿,抱起你来用鼻子在你身上乱拱,还一个劲嗲声嗲气地哼叽着“噢,喔呀,嗯,心宝宝,肝宝宝,肉宝宝”,这样的待遇你可享受过?
我慢慢地从一只金贵的小黄犬长成了一条毛色平庸的老黄狗,那模样就像是一只安哥拉猫同一箱柠檬杂交的产物。不过我的女主人从未意识到这一点。她认为诺亚当年放进方舟里的那对原初小狗是我祖先的旁系。她曾带着我到麦迪逊广场花园去竞争西伯利亚纯种猎狗奖,结果被两个警察挡在外边,连进都没进去。
我得跟诸位说说这套公寓。这样的房子在纽约有的是。门廊的墙面用帕罗斯大理石铺成,一楼地面用碎卵石铺成。到我们的房间去需要——哦,不是上三层——爬三爬。我的女主人租房时没要求配备家具,几件日常用具都是自己带来的——一九零三年款的制式古朴的带套垫客厅坐具,绘着哈莱姆区茶道室艺伎的油彩石版画,橡皮假花木和丈夫。
对天狼星发誓!这个两足直立行走的动物真让我为他感到悲哀。他是个瘦小男人,一头土黄色头发,胡子跟我的差不多。问他惧不惧内吗?——唔,巨嘴鸟、火烈鸟、鹈鹕都敢来啄他。他得负责洗盘子。还得洗耳恭听我女主人的唠叨,唠叨二楼那个穿鼠皮大衣的女人净往晒衣绳上搭不值钱的破衣褴衫。每天一到准备晚饭的时候,她总要打发他牵着绳子带我出去溜达。
如果男人们晓得了女人独自待在家里时如何打发寂寞时光,他们就会永远也不结婚。劳拉·丽恩·吉贝总是不住嘴地吃花生脆片糖,还时不时地往脖颈的肥肉上抹杏仁霜。盘子碟子她是不会去洗的,好抽空儿跟送冰的人聊上半小时,再找出一包旧信来读一读,还要就着泡菜喝两瓶啤酒。她每天必做的另一件事是扒着窗户从遮帘孔里向天井对面的公寓窥视一个小时。这就是她挨度时光的全部内容。在他下班回家前的二十分钟,她才把房间稍事整理,固定好假发卷,然后拿出一大堆针线活儿来干上十分钟装装样子。
我就在这样一套公寓里延续着我的狗命。几乎是整天趴在我自己的角落里看着这个胖女人消磨时光。有时我也打个盹,梦想着自己在外面飞跑,把猫儿们都赶到了地下室,还冲戴着黑色连指手套的老妇人汪汪叫,极尽一条狗应尽的职责。可她一会儿就得将我一把抓过去,对我心肝宝贝呵冷吹热喋喋不休地说一大套废话,还吻我的鼻子——我有什么法子呢?狗嘴里又吐不出象牙来。
既然追不成猫,我就为那做丈夫的哈比难过。我们俩的模样是如此相似,连大街上的人都看出来了。故此我们上街时只好躲开那些奔驰着阔气车马的大道,转而去穷人居住区的胡同爬去年十二月份的积雪。
一天傍晚,我们如此这般地在外面溜达,我尽量装成一条非凡的圣伯纳德种的狗,那老头儿也摆起架势,装出其身份和艺术鉴赏力都配得上听一位风琴手演奏门德尔松婚礼进行曲的样子。我抬起头看着他,用我的方式说:
“干吗那么愁眉苦脸的,你这个用麻包裹起来的窝囊废?她从不在你身上乱吻。你也用不着像我那样非卧在她腿上听她唠叨不可。她的唠叨能编成一本音乐喜剧,听起来又像是爱比克泰德的箴言。你应该庆幸自己不是一条狗。振作起来,本尼迪克,把颓丧抛开吧。”
这个婚姻上的倒霉蛋把头一低,仿佛人通狗性地看着我。
“哈,狗儿,”他说,“好狗儿。你都快能说人话了。你说什么呐,小狗?你在说猫吧?”
还猫呢!还能说人话呢!
这也难怪,他没法听懂。人类理解不了动物的语言。人与狗只有在文学作品里才能相互交流。
住在我们对面的那位夫人养了一只黑棕相间的小猎犬。她丈夫每天傍晚也牵着它出去,可他却总是高高兴兴地吹着口哨回来。一天,我在走廊里跟那只黑棕花斑狗碰了碰鼻子打了声招呼,要求他解释一下个中原委。
“喂,那个蹦蹦跳跳摇尾巴的,”我说,“你知道,一个男子汉在大庭广众之下充当一只狗的保姆这太不正常了。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哪个牵着汪汪狗在街上走的男人不想揍瞧他热闹的人。但是你那位老板子每天回来都是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就像一个业余魔术爱好者在变鸡蛋戏法儿。他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别对我说他真心喜欢干遛狗的活儿。”
“他吗?”棕斑狗说。“哦,他服用了一种天然补药。他把自己灌醉。我们出去刚到街上的时候他同样是羞羞答答小心翼翼的,像个开汽艇的人,又像个打牌不敢冒险下注的人。等我们串了八家酒馆之后,他就不管绳子的另一头儿拴着的是一条狗还是一条鲇鱼了。有一次我自顾自地从旋转门往外钻时竟把尾巴挤掉了两英寸。”
小猎犬提示给我的这条路子——挺好玩的,不妨学着去干——使我思索起来。
一天黄昏,大约六点钟,我的女主人吩咐他抓紧时间带贝贝出去呼吸新鲜空气。此前我一直没向诸位交待,那是他们给我起的名字。那只黑棕色小猎犬的名字则叫“欢欢”。我想要是比赛追兔子,我准比他强。无论如何,“贝贝”之类的名称总是有伤自尊。
我们沿着一条行人稀少的马路来到一个僻静的地方。我见时机一到,便拉紧狗主人手中的绳子,在一家十分引人注目的雅致的酒吧前停下来。接着我四腿用力死命往门里拽,还狺狺哀鸣,就如同报纸上新闻快讯所报道的那条救命犬一样。那条救命犬之所以哀鸣,是为了告诉家人小艾丽丝在溪水边采百合花时陷到泥沼里去了。
“嘿,该死的,没错儿,”老头儿咧开嘴笑了;“要不是这个跟一瓶柠檬矿泉汽水似的黄毛小子想请我进去喝一杯才怪呢。让我想想——我有多长时间没来这儿磨过鞋底子了?我肯定会——”
我了解他,这一点我心里非常清楚。他要了一杯热苏格兰威士忌,在一张桌子旁坐下来。整整一个小时,他像过节一样忘情畅饮。我呢,就蹲在他身边,不停地冲侍者摇尾巴。在公寓里吃妈妈推着手推车在爸爸回家前八分钟从熟食店买回来的东西,跟在酒馆自由自在地进餐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等把苏格兰特产享用一空,桌上只剩下黑麦面包的时候,老头把我从桌子腿上解开,像渔者逗弄他钓上来的大马哈鱼似的牵着我往门外走。到了店外,他解开我的项圈,然后把它朝当街狠劲一扔。
“可怜的狗儿,”他说;“好狗儿。她不会再乱吻你了。真可耻。好狗儿,去吧,去让公共汽车把你轧死吧,那样你就解脱了。”
我没走,而是围着老头的腿连蹦带跳,快活得简直像一条在地毯上做游戏的哈巴狗。
“你这个跳蚤脑瓜、捉土拨鼠的老家伙,”我冲他说——“你这个咬风吠月、只会嗅兔子偷鸡蛋的老猎狗,看不出来我不想离开你吗?你还不清楚吗?我俩都是被关在笼子里的小狗,女主人是位残酷大叔,她把洗碗布扔给你,在我身上抹灭跳蚤药,还在我尾巴上系了一个粉红色蝴蝶结。干吗不同这些一刀两断,从此我俩永远做朋友?”
诸位或许会说他听不懂——也许他的确听不懂。不过苏格兰威士忌使他感到了几分酒意,他站稳身子,默默地思忖了一会儿。
“狗儿,”他最后说,“我们活在世上不可能有十几条命,也没有哪个人能活到三百岁以上。我要是再去看那房子一眼就是蠢猪,你要是去就更蠢;这可不是说着玩的。我敢以六十赔一打赌,要是到西部去,嗬,准能一帆风顺大获成功。”
没有绳子拴着我了,可我还是欢天喜地紧随着主人向二十三号街渡口走去。沿途的猫有理由庆幸自己长了两对识趣的爪子。
到了泽西区那边,我的男主人对一个正站着啃葡萄干甜面包的陌生人说:
“我和我的狗,要去落基山区。”
不过最令我高兴的是老头儿揪住我的两只耳朵把我拽得直叫唤并对我说:
“你这个不起眼的猢狲脑瓜、老鼠尾巴、不黄不绿的受气包,知道以后我要管你叫什么吗?”
我想到了“贝贝”,便悲哀地哼叽起来。
“我要管你叫‘彼得’,”我的主人说;此时此刻,我即使长出五条尾巴来一起用力地摇,也表达不尽我内心的喜悦。
大家还在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