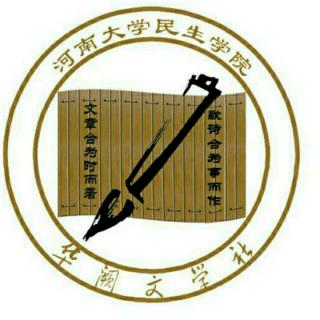
介绍: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由河南大学民生学院华阙文学社新媒体部门举办的千芊阙语节目。今晚为大家分享一篇文章。
她的自我介绍没有一点多余的废话,看上去是爽快的人。
“喵,你好。”她就这样边说着边坐在了我面前的椅子上。
我在图书馆最靠近窗户的位置上坐着,如果只是想要找人闲聊,也有点太刻意了。
她说话的声音刚刚好,既让我听的清楚又不会打扰到其他人。
还有,她为什么叫要学猫叫呢?
我一头雾水,快速地扫了一眼手中《挪威的森林》,又抬头看面前的女孩。
女孩露出缺了一颗犬齿的洁白牙齿,灿烂地笑着。
“你认识我?”我问她。
她的笑容顿了顿,随后点了点头。
“出去说?”
她点了点头,将垂下的发髻撩回耳后。
于是,我们并排走到楼下,不知为何,这个学着猫叫的女孩走起路来总给我一种一蹦一跳的趋势,但又并非如此,只是脚步轻快,但巧妙得声音不大。
她穿着有些宽大T恤衫和五分牛仔裤,脚上是一双我从未见过的牌子的运动鞋,其余便再无修饰,皮肤发出健康的红色,头发稍短,盘在脑后。
觉察到我的目光,女孩转过头,对我漂亮的一笑,缺了的那颗牙齿在她精致的脸上似乎更显俏皮。
于是,我坚信了心中的想法:自己从未见过这个女孩,也不会在冥冥之中于这个女孩有过怎样的交集,不知为何,在楼梯上下交错的十几秒间,我便坚信不疑。
下楼后,我把书与借书卡一同交给管理员,戴着黑框眼镜的瘦小中年人透过斜眯着的眼睛盯了我好一会儿,又看了一眼我身旁的女孩,不知是否天生就这样一副诡异的像是含着苦瓜汁的面容。
磨蹭了半天,我终于从苦瓜汁中解脱。
“这人看上去好凶啊。”女孩说着,看来不只是我一人头皮发麻。
大概是我也露出了为难的神色,女孩“嘿嘿”地笑了。
“所以...”走出图书馆,我问女孩。“你找我什么事?”
女孩带着奇妙的笑容,没有看我,脚步也没有停,我只得跟上她。
走过树荫,我期待着能有阵风给这条杨树林组成的林荫路带来些“沙沙”的生机。
可惜没有那阵风,在临近午睡的困倦时分,连个人影都没有。
我想说些什么,但又无话可说。
女孩仍面带微笑,一蹦一跳地踩在落下的叶子上,啊...只是脚步轻快,连叶子都没有喊疼。
“嗳。”
终于,在到最后一棵树之前,女孩终于开口了。
“呼——。”我不觉间真的长出了一口气。
“你还是记不起我吗?”在树荫与阳光的分界点,女孩停住脚步,蓝色运动鞋划出一个半圆的弧度,面对了我。
我想了一会儿,大概在某个瞬间达到了绞尽脑汁的程度,但我之前就已经认定:我肯定从未见过她。
我抱歉地摇了摇头。
她露出了失望的神色,随后便像无所谓一般挥了挥手。
“没事,只要一起去吃饭就行了。”
“吃饭?”我顿时有些莫名其妙。
“没错,吃饭。”女孩边说着,一脚踩进幽深的阳光里,我又只得跟上,并且开始怀疑她是否知道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或者是我忘记了一些我该知道的事。
不过,忘记也没有办法,毕竟,我是个病人嘛。
“高雪症对吧。”像是知道我在想什么,女孩说道。“所以记不住我。”
狼癍,高雪症。
一个无法治愈,不停的衰减我的免疫系统。
一个很难治愈,不停的攻击我的免疫系统。
于是,我会经常忘记一些事情,但大多是无所谓的小事。
医生无能为力,没有任何药物能够增强免疫力,唯一一个可能有用的,便是蛋白质,
我晃了晃腰上的小背包,里面发出胶囊碰撞药瓶的沉闷声响。
里面还有大量的布洛芬,来缓解我的头痛。
从每天早上起,我的头就一直如针刺般的疼痛着。
来到熟悉的餐馆,女孩没有任何迟疑,找到了一个我平时经常坐着的座位,同样是靠近窗口,唯一不同的是窗口上盛开着一朵水仙花。
“看,你总是在这吃饭吧。”
女孩似乎很了解我,我和她面对面坐了下去。
我笑了笑,拿起窗上的花洒,为水仙浇水,不知谁在花盆边缘的泥土里放了一张纸鹤,我随手将它扔到了垃圾桶里,花朵上的水滴发出生动的光泽。
自始至终,女孩都静静的看着我,脸上不知是无奈还是什么的别样神情。
看来是真的不小心把她忘了。
“对不起,那能告诉你的名字吗?”
我边说着,边在腰包里翻找着笔记本,这是我找回记忆的唯一途径。
“在里层的兜里。”
女孩看着我,又换成了一副饶有兴趣的神色。
我可能比我想象中跟这个女孩更有关系。
我打开笔记本,第一页只写了一句话:
放在里层的兜里,不要再忘了!
在我困惑和苦恼的时候,女孩已经点好了菜,老板娘端上了一碗牛肉饭,里边放了辣白菜。
没错,这也是我经常吃的。
身材臃肿,满脸皱纹的老板娘对我熟络的笑了笑,随后像是没看见女孩一般面无表情的离开了。
我翻了翻笔记本,上面的大部分事情我都记着,比如把钥匙放在哪,银行卡的密码,父母的手机号,但也有些小事忘记了,比如借了某本书,和某个朋友说了话,写了某些东西之类的。
但我忘记的事情这在厚厚的一本事情中仅仅只是九牛一毛,而且,我清楚的记得我每天都会看这本笔记本,并且记住的事情都是一样的,而忘记的大概也都是一样的。
可无论怎么找,都找不到关于这个女孩的事情。
如果我真的见过她,我一定会把她缺了的那颗牙齿和漂亮的脸写上的,但笔记本上并没有这些。
我抬起头,有些困惑的盯着面前的女孩。
似乎是早就料到,看到我抬头,女孩便也从大碗拉面中抬起头来,露出那个奇妙的笑容。
“找完啦,还是先吃饭吧。”女孩说。
“所以你还是先把名字告诉我吧,不然我真的想不起你。”
“我说了啊。”不知为何,女孩回答的时候似乎有些慎怪的样子。
“你说了?这是什么意思?”我越来越摸不清头脑。
女孩皱了皱眉头,手上的筷子有一下没一下的在拉面碗中搅拌着。
看到女孩的反应,我猜大概又让她失望了,于是也不再说话,大口吃着牛肉饭和辣白菜,直到辣味呛的自己有些鼻塞。
“咳咳...”我忍不住咳嗽了几声。
“唉...”女孩看着我,终于露出了无奈的笑容。“慢点吃。”
“每次都这样。”女孩不易察觉的小声说道。
我装作没听见,一边喝水一边拼命回忆面前的女孩。
然而相伴而来的便是更加剧烈的头痛。
我从腰包中掏出药瓶,乳白色的胶囊颗粒顺着喉咙消散进胃里,这些蛋白质或许对我的头痛没有任何作用,因为医生真诚的告诉我,这只是“安慰剂”而已。
“有多痛?”女孩问我。
我看着她,停止了思考。
“像忘记一个人一样疼。”
吃过中饭,太阳沉落的很快,刺眼的阳光成了昏暗的底片,我和女孩走在回学校的街上。
“抱歉,还是想不起你。”我对女孩说。
“嗯。”她像是理所当然般点了点头。
忽然,女孩转身面向我,她似乎很喜欢这种说话方式。
“但你能记住我吗?”女孩认真的板着脸,直视我的眼睛。
“当然。”我可以记在笔记本上,但当我把手伸向腰包时,女孩突然抓我的手,我吓了一跳,抬头看她时,猫的眼中带着忧伤的神色。
“你每天早上都会坐在图书馆靠窗的位置...”
“你每天都在看《挪威的森林》...”
“...”
我不记得看过《挪威的森林》。
“你每天借同一本书,却总不明白为什么管理员那么看你...”
“...”
我有些难以接受,我以为我已经把所有的事情都记在了笔记本上。
“你每天都去同一个餐馆,每天都给水仙浇水,每天都要把千纸鹤扔掉...”女孩继续说。
这些我都记得。
“你每天都会忘记笔记本在里层的兜里,每天想不起我都会大口吃饭,经常呛住自己...”
每天...
这是什么意思...
“我每天...每天...问你”她哽咽着,像是要哭出声来。
“你...你都会说:像忘记一个人一样疼!”女孩无力的放开我的手,瘫坐在了花坛边,泪水如泉涌般划过脸颊。
我愣在原地,不知该说些什么。
“你说,你绝对不会忘记我。”
“只要我学猫叫,你就能想起我;只要我们一起去原来的餐馆吃饭,你就能想起我;只要你看到千纸鹤,你就能想起我...”
她的声音越来越小,终于不再说话。
我的头痛前所未有的愈加强烈。
终于,良久过后,女孩平静下来,站起身对我说。
“可世界不会有永远爱你的那只傻猫的...”
“对不起。”我不知该说些什么,只有站在原地。
我想不起来,什么都想不起来。
女孩面无表情,精致的脸上带着泪痕, 从我身旁走过。
“不要记下我,我不会再来了。”
轻巧的脚步越来越远。
当我从混乱如荆棘般的思绪中回过神时,路灯已经亮起来了。
我应该记下来,我想。
可我要记下什么呢,我和她究竟有怎样的故事,可我甚至连她的名字都无从记起。
“头好痛...”走向深暗的前路,我禁不住喃喃吃语。
“喵,你好。”她就这样边说着边坐在了我面前的椅子上。
我在图书馆最靠近窗户的位置上坐着,如果只是想要找人闲聊,也有点太刻意了。
她说话的声音刚刚好,既让我听的清楚又不会打扰到其他人。
还有,她为什么要学猫叫呢?
我一头雾水,快速地扫了一眼手中《挪威的森林》,又抬头看面前的女孩。
女孩露出缺了一颗犬齿的洁白牙齿,灿烂地笑着。
“你认识我?”我问她。
她的笑容顿了顿,随后点了点头。
“出去说?”
她点了点头,将垂下的发髻撩回耳后。
结尾语: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大千世界,千芊阙语。欢迎喜欢声音热爱文字的每一位小耳朵加入我们,千芊阙语交流群群聊号码:710802265
大家还在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