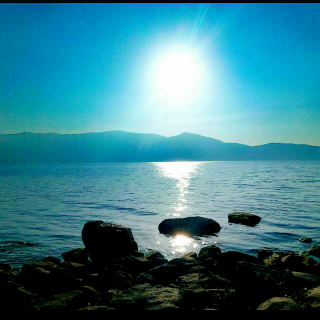
介绍:
我忘记了凌晨有巴萨与马竞的决赛,却记得8点要准时上班,没有了少年时的勇气,面对的困难却要比那时候多得多。人需要多少时间才会习惯这样一种生活,将吃饭与工作当做生活的中流砥柱,忘记音乐、书籍、烈酒与通宵。其实也不用多长时间,当你拥有着同别人一样的生活方式,与他们一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是一种无形的暗示,不用你去刻意维持,潜移默化地消磨了自己的特性,成为芸芸众生里的一位。世界是一方囚笼,而习惯则是慢性毒药,人群是媒介,传统是根源。
经常会站在落地窗前,看着楼下车水马龙的十字路口,为了生计、为了孩子、为了工作,每个人都有足够的理由行色匆匆,有没有想过恰恰因为这些太过充分的理由,让我们在这匆忙的人群中迷失了自己。因为这些理由太过相同或者大同小异,就是这样的形貌相同原因,使得自己的特性被抹灭在群体中。在一个久远的雨夜,听着急雨打在屋檐的声音,摸着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觉得世界好似只剩下自己,那种独一无二的感觉新鲜且充满诱惑。从客观上说我永远不能独一无二,从主观上说我们每时每刻都在独一无二,是不是因为这压抑且快节奏的生活已经将你主观上的优越感消磨得一干二净,所以常常觉得事不如人,进而像通过外在的物质优越感去满足这种空虚,到头来却让自己更加劳累,离我们的初衷渐行渐远。也许这篇文章的题目取得不够好,因为世界从来都不是一座囚笼,我们只是从心底为自己画了一个圈,然后自己囚禁了自己。
有一个朋友一生挚爱云南,终于在自己23岁的时候踏上了旅途,只有大巴、背包与青旅,去参观“大祭风”的途中遇到泥石流,当时他就坐在司机边上,看着司机双手颤抖的握着方向盘,那时他才发现生命本身没有那么繁琐,生活也不再是生计、婚姻、孩子、交织成的一团乱麻,生命在这种情况下变得很干脆,只有两个单纯的选择-死去或者活着。另一位朋友用辛苦一年攒下的钱,买了自行车,购置了装备,走上了骑行这条不归路,半年后见到他,觉得他不是去了西藏倒像是去了非洲。他同我说我蜷缩的活了二十年,却不知道世界其远,每天都有纯净水喝的日子,不懂得两天没水喝辛苦,看惯了高楼与烟筒的人,不知道风马旗飘扬的天空看起来举手就能触碰。
我们被囚禁在城市,囚禁在自己狭小的生活圈子里,让我们以为世界就是简简单单的功名利禄,就是二十四小时的热水,或者柔软的床垫。臆想着满是朔风的西北夜晚是怎样的孤独与寂寞,从而害怕被舒适自足的生活抛弃掉,进而落魄被人不容。这也许是人之常情,不过更可能是我因为把世界看得过于狭小后的受迫害妄想。老一辈人更重生计,或者尊奉父母在不远行的孝道,不过他们的少年有着广阔的田野,可以任他们驰骋。我们有什么,学校?它只有百倾。教室,它能有几方?远行是生命的一个过程,而漂泊则是人的本性。
最难忘的是一次夜宿时看到的门帘,旅店是老板用仓库改建的所以很是简陋,实在将就不下,要走的时候却看到那幅门帘。门帘上画着的不是常见的粉红碎花,而是颜真卿的《劝学》“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因为是颜真卿的诗,所以必然是颜体,不是大家之作,却是独有风骨,更难得是这作品不是拓印也不是复印,而是亲手所书,必然是书法的发烧友所作。老板不是优渥之家,能习的这手好字必然是真的爱这口,在这般物质横行霸道的年月,不因自身贫寒而忙于生计,却在这书法之中寻得安慰。喜欢这种人生态度,所以欣赏以此为生的人。所谓自由,不是如《在路上》一般,经年漂泊、时常吸毒与滥交,“闲来诵黄庭,寂寞读南华”,便是对自由很好的解读,这样的人生也不至于沦落到整日庸碌或者徒自放纵。终日困窘的蜷缩在弹丸之地,将这偌大的世界活的窄狭,是时代与历史给予现代人们的宿命,但并不妨碍你以宽广的眼界看世界,若真正将这广阔的世界当做囚笼,本是一种另类的自由。
大家还在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