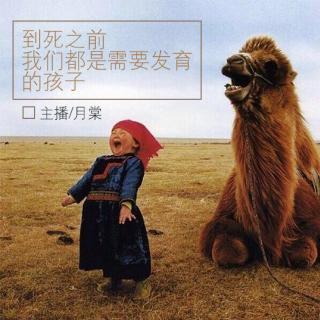
介绍:
到死之前,我们都是需要发育的孩子
文/蓝纹奶酪 编辑/若辛 主播/月棠 后期/大天
在这个令人感到沉闷的秋天的午后,我坐在学校图书馆的顶楼读完了《阿弥陀佛么么哒》这本书。合上书,我抬头,厚厚的乌云沉沉地压在头顶的天穹之上,似有一场大雨将至。但心中早有一场大雨浇下,如醍醐灌顶,劈头盖脸。
大冰说:“可不可以绑紧鞋带重新上路,去寻觅那些能让自己内心强大的力量,愿你我可以带着最微薄的行李和最丰盛的自己在世间流浪,以梦为马,随处可栖。”大冰的人生就是一场流浪式的人生体验。有种流浪,是一路走一路唱一路疯狂,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投奔,由内向外的寻找,彻头彻尾的不卑不亢,不紧不慢的沉淀与磨炼,一往无前的骄傲不羁,是一种一路逆着光,逆着冷眼与嘲笑,穿过人山人海,越过山河大海,在风雨如晦里呛声大喊,奔向未知的远方,与另一个自己,真正的自己欣喜相逢的奇特旅程,是一种挣扎着把苦难当成乐趣经受品尝,清出一片透明无尘的心地的漫长修行。
《搭车去柏林》之后,无数人纷纷辞职去旅行,在城市里呆久了的人们被一股强劲的思潮煽动起来,“有些事现在不做,也许就永远没有机会做了”,仿佛在一夜之间,全世界的白领都开始着手准备自己的间隔年旅行了,所有的大学生都开始背上背包骑行了,陈绮贞的音乐一下子变成了小清新的标志,节假日的318国道忽然开始如集市般拥挤,城市里过惯了小资生活的年轻人打了鸡血一样地从四面八方奔向拉萨,涌向凤凰,飞往丽江。接受了一番灵魂的洗礼或者刻骨铭心的艳遇之后,回归各自的生活,生活还是那个生活,但内心深处却隐然有些东西不一样了。是什么不一样了呢?
没什么不一样。不过是一场心灵上的自慰而已。在我看来,于大冰,卓玛央宗而言,他们的旅行更像是修行,他们渴望那样去活一次,于是就去了,这是放浪形骸的洒脱,亦是对自己生命的一次深入探讨。于更多人而言,旅行是为了抚慰心灵,感受自然和文明的力量。而那些视所生活的环境如樊笼的所谓精英们,也许在日复一日单调的工作和麻木的生活之后,他,他们究竟是怎样开始困于心而衡于虑的呢?
我想试着探讨一下。就像大冰在”一席“的演讲中所说的一样,我们这个社会是一个有点儿扯淡,一个十分悲凉的社会。社会的悲凉从每一个感到困惑,感到迷茫,感到压力沉重如山的年轻人身上折射出来。家庭,家族,亲朋甚至我们所有的交际圈都会赋予我们各式各样的身份和标签,不论你承不承认,这确实是一个以标签来界定一个人的社会。但是,真的需要标签吗?
这本书里给了我们一个多元的回答。这书里的一群人看似各有各的生活,各有各的不同幸福,但其实他们有一个共通点,那就是遵从自己的内心。他们比任何人都知道自己想要的生活,他们总能够从万千不如意中找到自己的幸福。这是十分健康且质朴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但是我们的社会却似乎在日渐膨胀的物质生活中逐渐将它遗忘了。这是人类流传已久的传统,到了今天却成了离经叛道。
我忽然想到韩寒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如果一个人十八岁之前还不知道自己的理想是什么,想要的是什么,真不知道是他自己的悲哀还是中国教育的失败。”貌似我的很多同龄人都处于这种悲哀之中。全世界都告诉他们,上大学之前一定要为了高考这唯一的一个目标而努力,以至于他们在考上大学之后才开始着急忙慌地去为自己的人生确立目标,寻找方向,少数人找到了自己的方向,但更多的人是在利益权衡的加减法,在二十岁的年纪里计划自己以后三十年的人生,化为一滴与他人无异的水,在社会与现实的横流中身不由己地跌宕起伏。
其实我更愿意用一个寓言来诠释我欣赏的那类人,这个寓言是韩寒写的。
这么多年来,一直是我脚下的流沙裹着我四处漂泊,它也不淹没我,它只是时不时提醒我,你没有别的选择,否则你就被风吹走了。我就这么浑浑噩噩地度过了我所有热血的岁月,被裹到东,被裹到西,连我曾经所鄙视的种子都不如。
一直到一周以前,我对流沙说,让风把我吹走吧。流沙说,你没了根,马上就死。
我说,我存够了水,能活一阵子。
流沙说,但是风会把你无休止的留在空中,你就脱水了。
我说,我还有雨水。
流沙说,雨水要流到大地上,才能够积蓄成水塘,它在空中的时候,只是一个装饰品。
我说,我会掉到水塘里的。
流沙说,那你就淹死了。
我说,让我试试吧。
流沙说,我把你拱到小沙丘上,你低头看看,多少像你这样的植物,都是依附着我们。
我说,有种你就把我抬得更高一点,让我看看普天下所有的植物,是不是都是像我们这样生活着。
流沙说,你怎么能反抗我。我要吞没你。
我说,那我就让西风带走我。
于是我毅然往上一挣扎,其实也没有费力。我离开了流沙,往脚底下一看,操,原来我不是一个植物,我是一只动物,这帮孙子骗了我二十多年。作为一个有脚的动物,我终于可以决定我的去向。我回头看了流沙一眼,流沙说,你走吧,别告诉别的植物其实他们是动物。
一一摘自韩寒《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
我喜欢故事,我喜欢听各种各样的人讲故事,但大冰的故事却有着和其他任何讲故事的人都不一样的光芒和色彩。他讲的全都是真实的故事,真实得我可以感受到那些故事的骨骼脉络,血肉鲜活。这个世界上有太多意想不到,现实总是比小说更像小说。他像一个坐在桌子对面的老朋友一样,压低帽檐,点起一支烟,嘴角露出一丝苦笑,云淡风轻地把他和他的朋友们跌宕起伏的半生解剖在你面前,仿佛把他们的青春和热血、眼泪和欢笑当做一顿丰盛的晚餐与你分享。
大冰在另外一篇文字里曾说:
“那时候我们怎么那么直接啊 直面一切
体内流淌的血液都是有温度的
随随便便就敢去眺望所谓的远方
直面一切的时候 都是理所当然的积极
什么都敢诉说
什么都敢歌颂
一切的出口都指向真爱和自由”
大冰的文字是有温度的,这些故事也是有温度的,如口中缓缓吐出来的烟圈,缭绕在心头,久久不散,让我也感受到了那种滚烫的如同烙印般的温度。也许这十年他遇见了太多有故事的人,经历了太多的故事,它们有些随风消逝在了时光里,但更多的沉淀在了记忆中,它们满的快要溢出来,以至于他不得不挑拣一些掏出来晾晒晾晒,然后重新贮藏。他随口的一两句感慨也充满哲学意味,这么多年的动荡漂泊让他成了一个仍有困惑的智者,虽然仍有困惑,却能为我们年轻人指点一二。我觉得我应该感谢他能够把这些东西写出来,佛讲慈悲,我不对佛家不甚了解,但我想,也许这就是他的业障和慈悲吧。这些故事让我感受了来自内心的力量。左小祖咒说世界上分三种人:勇者吃肉,智者吃骨,无敌者是什么都不吃的。他们什么都不吃,靠内心的力量活着,他们是无敌者。
大冰说,那片艽野,是他精神上的原乡。那片艽野当然不是陈渠珍和西原的艽野,而是他十年的漂泊时光,那个背着手鼓浪迹天涯的孩子,西藏瓦蓝的天空下明晃晃耀眼的阳光,那些教会了他成长,教会他爱,却再也不会回来的人和事。那些青春里的故事是我们最宝贵的东西,谁都不会随便提起,但也没有人会轻易忘记。
我正经历着这样的青春,不敢奢谈怀旧,俗话说的好,老思既往少思将来,思既往故生留恋,思将来故生希望。我不知道能够在自己的那片艽野上走多远,是否能够留下些雪泥鸿爪,但那又有什么呢,我享受的是这个过程。我有一颗乐观和勇敢的心,我还需要什么呢?
幸福的出口并不单一,简单的生活有时也真的触手可及,但我们仍然要努力地去生活,因为年轻时,总有一片艽野,在等着我们去跋涉。
因为到死之前,我们都是需要发育的孩子。从未长大,也从未停止生长。就算改变不了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别想将我们改变。
————————————————————————————————————–
如果有一天你找不到我
你会去什么地方发呆
谁说月亮上不曾有青草
谁说可可西里没有海
谁说太平洋底燃不起篝火
谁说世界尽头没人听我唱歌
谁说戈壁滩不曾有灯塔
谁说可可西里没有海
谁说拉拇拉措吻不到沙漠
谁说我的目光流淌不成河
谁说我的一生注定要蹉跎
谁说你的心里荒凉而曲折
谁说流浪歌手找不到真爱
谁说可可西里没有海
陪我到可可西里看一看海
我不要未来 只要你来
陪我到可可西里看一看海
我一直都在 只要你来
陪我到可可西里看一看海
大家还在听

